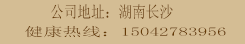![]() 当前位置: 库克群岛 > 自然资源 > 随便聊聊2017年去过的几个地方
当前位置: 库克群岛 > 自然资源 > 随便聊聊2017年去过的几个地方

![]() 当前位置: 库克群岛 > 自然资源 > 随便聊聊2017年去过的几个地方
当前位置: 库克群岛 > 自然资源 > 随便聊聊2017年去过的几个地方
原本想继续更新在库克群岛的故事,但一看时间,已经到年年末了…而去库克群岛那是年8月时候事了~
不禁对自己发出一声冷笑~(我知道你也在鄙视地笑我…)
其实,和Daisy的南太平洋环游差不多在一年前就已经结束了…期许着还能在年一起去瓦努阿图、汤加、纽埃看看,但或许会是每年许下的上一年未实现的愿望吧…
然而,回想整个年,我也没停下脚步,依旧在“跑”,陆陆续续去了尼泊尔、蒙古、越南、斯里兰卡和土耳其。
大部分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也比较少分享,但今年去的这些地方却很想和朋友们叨叨。
这些地方都经历过天灾人祸,是很多人想去又不敢去,到达时会有些嫌弃,或有些小胆怯,但去过后就会还想再去的地方。
那里的人眼神里自带忧郁、无奈、悲伤,但他们却勤恳、乐观、怜悯他人地生活着,我倒觉得他们是真正“佛系”人。
由于工作时,我接触最多的就是向导和司机,他们是我观察和了解这个地方以及人的核心。
如果说,年的旅行是不同的“家庭”,让我在和他们的生活和相处中认识这个地方,感受到不同文化下的“家”。
那么,年是旅行中的“向导”让我感触到一个国家的命运对人的影响。他们的身上有很多的共性:常年不在家,在家太久又担心没收入;生活不算富裕,但也自己的小资追求;热爱小动物,尤其是猫猫狗狗;为人坦白诚恳,聪明好学;乐观积极地为人处事,但悲观地看待世界和人生。
尼泊尔:
自尼泊尔地震后,这个国家的旅游行业就一落千丈。在加德满都仍能看到很多断裂的道路、房屋和神庙。
很多人会觉得尼泊尔被毁了,但我却觉得那些原本的完好的建筑在断纹下更具有魅力,就像身上有了伤疤人才能让自己更完整。
更何况尼泊尔魅力不仅在宗教上,他本身就足够吸引人。
据说,今年尼泊尔旅游行业有所回暖了。
我的城市向导Bipin,一脸的书生气,大学毕业后就做了向导。大地震发生之时,他正好在送客人去机场路上。当时电话,交通都瘫痪,自己骑了摩托直往家赶看妻女是否安好。
人没事,房子全塌了。
Bipin说的时候脸上仍旧带着礼貌地职业笑容,地震对他来说好像也不是很大的事情,他说历史上来看,尼泊尔每隔几年就会有一场大地震。
地震后的一年里,Bipin都没有工作,好在他所在的旅行社咬牙仍旧给他们发基本工资。他也陆续收到一些欧美客人的捐款,加上贷款和积蓄,盖起了三层楼的新房子。今年年初去时,他说还有一层还没钱盖,希望今年能盖上。
队员问他是不是因为信仰让他们变得处事不惊,他倒坦率地说,和信仰没有关系,尼泊尔人天生就这样,没有想不开的事。真不知道他是在客套回应还是真心的,我们也只能囧笑。
路上Bipin看到小狗就要抱起,紧靠着他的脸求合照,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他说就是喜欢;看到二手书店,就会翻阅两下,看看有没有有兴趣的。
他也算尼泊尔的城市孩子了,没怎么爬过山,更没见过什么雪。但万万没想到,今年年初尼泊尔山上下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整个徒步变成了雪山徒步,大家都没准备,让我也有些措手不及,不知怎么做到最安全。Bipin倒是像个孩子一样,因为从未见过这么大场的雪,非常兴奋。
但在徒步时,我们另有一个向导Buwan和随行的背夫们,他们不仅一路扛着我们4天的行李,衣着也非常简陋,鞋子更是没什么防滑、防水的讲究,能穿着走就行。
Buwan是整个背夫队的头头,他已经也坐着和Bipin一样的导游工作,但他又另考了徒步向导证,这样两边都可以做。做徒步向导对他来说,体力上要比背夫轻松,但精神压力更大,一个人要安排好游客和背夫所有的行程和情绪。最重要的是,这些背夫大多都和他是同村的,他要让他们都有活干,否则只能种地挣更微薄的收入。
Buwan的努力其实是供正在私立学校上学的女儿,他有两个孩子,儿子还小。他总是会和女儿分享他见过的世界各地的人,希望她也能走出这里,去那些地方看看,但一定要学好外语。
近些年,越来越多地中国游客来到尼泊尔,他很想女儿学好英语和中文,他自己也希望有机会去中国进修中文,但一切还要看工作上是否有这个机遇。
蒙古:
这个地方又熟悉又陌生,它和内蒙古接壤,说的语言都是蒙语,但文字却是俄文。
整个国家已经是民主国家,但城市发展的状态、建筑形态,仍旧像80、9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全民的信仰是佛教,再荒凉的草原也会看到一个佛塔。如果看到佛庙,那里一定有人群居在这里。
很多旅行者因为搭乘贯穿亚欧的西伯利亚列车来到蒙古,因为它是必经之地,成吉思汗时期曾经的辉煌也增添了神秘感。
我去的3月并不是旅行的好时节,冰冷的天气加上昏黄的草原与土地,显得更加荒凉。
但自认为蒙古人应该和这枯凉的天气相反,狂放不羁地马背上的民族,应该和内蒙古人差不了多少,生性刚烈,热情又不拘小节,晚上一定酌上两口干烈的高度白酒。
事实上呢?
路上的大部分行人的表情都非常严肃,加之由于蒙古人颧骨高、脸型长、眼睛小的长相特点,当他们下垂着嘴角,用聚光的眼神盯着你的时候,非常不自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什么了?
在街上,学生模样的路人对于外国面孔,会羞涩在一旁商量要不要上去搭讪下。而中年人对于外国面孔总是瞥一眼,有种“跑来这干嘛,懒得理你的”眼神独白。他们似乎更好奇的是,和西方人走在一起的亚洲人,我就深有感受。
由于在乌兰巴托同行的都是西方人,我和他们走在路上时,常常被当地人盯着看,他们甚至好奇地问我身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晚上的蒙古更是一个空置又黑漆漆的冰冻室,并没有看到哪家再啃着羊肉喝着白酒,都是老外们在唱着当地成吉思汗牌的白酒。
稍显意外的是,韩国文化在那里极为受追捧。晚上最热闹的地方是韩式料理餐厅或者韩国人开的卡拉OK,最热闹的咖啡店也是韩国风格的,年轻人的穿着打扮也都是韩式的大衣和太阳眼镜,路上看到大部分家庭的电视上也都放着韩剧。
如果想去酒吧嗨一下,或许会有些小失望。蒙古妹纸算是冷美人,即使会说英语,也客套两下就回自己的朋友圈了。在酒吧,两个加拿大来的汉纸跑去舞池搭讪美女,想多靠近点,女生们就转身下台了。相约女生喝两杯,也说要回家,或者要去找朋友婉拒了他们。
要说我在蒙古遇到最热情的女孩,应该就是在蒙古南部Gobi的向导Chuka。
要去Gobi之前,我就着年左右出版的蒙古LonelyPlanet试着打了一个Gobi的住宿的电话,电话那头说是乌兰巴托一家旅行社,并表示那里已经没有这家住宿了。但当我们到了Gobi下车时,却有一个女孩和一个大叔举着我的蒙古号码,在那恭候好久了!让我惊喜又惊吓!
下车就跟着我们,表示车和住宿,景点都可以安排。我挺抵触这样的热情,但也没有其他可联系的人,也就接受了她的安排。
Chuka的全职工作是在当地的学校做英语老师,到了旅游旺季做做导游。当我倒觉得老师是她的兼职,导游才是她喜欢做的。
我们前去的那几天学校也还在上课,她似乎很方便的就能空出时间。虽然我的英语也不算好,Chuka的英语水平在当地也已经算很不错了,但我感觉她的学生们应该不怎么运用英语。而我去到她的学校之后,那些学生的反应也让明白,他们和我的初中时代一样,只是应试学英语而已。
路上,Chuka总是很热情地说,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但常常不是没有get到我们的问题,就是她也不知道。
在Gobi旅程的最后一天,她执意要请我们吃饭。我们平时路上吃的都是她和司机自带的面,或者游牧人自己做的牛肉汤,饺子等,吃的特别简陋。而那晚Chuka一定要带我们去Gobi镇上最好的餐厅吃饭。
当那天,她稍微打扮了一下,但我们到达那家餐厅时已经关门了。我们想就此不必客气了,但她立即说还有一家开着,说一定尝尝那里的牛排,氛围也特别好,那里有蔬菜沙拉和水果。我们也不好意思再回绝。
那家确实是当地最好的酒店之一,直接建在了政府楼旁边,到达餐厅时,餐厅皮质的座椅,西式的装修风格,播放着爵士乐,里面用餐的人都是穿戴奢华、披着皮草、手提LV的贵妇,和小镇上朴实的色调和生活有着很大的反差。
连我自己都觉得,穿着4天没换洗,带着满身灰尘和沙的户外装的走进这样的餐厅有些格格不入。
而我感觉她是有话想说,才一定要请吃这顿饭。她自己先给自己点了酒,有些微醺后,就打开了话匣子。
Chuka来自蒙古南部很小的村庄,和家里人的关系不算好,不想蜗居在小镇里,读了师范大学后,就做了老师。现在在一个合租的蒙古包里住着。(我见过的蒙古包都没有浴室,卫生间都设在屋外,一个木棚里挖个坑而已。)
她说她的男朋友在美国,但是没有办法一起过去。因为要从蒙古去美国,需要很多证明和储蓄。她并不喜欢这个工作,做这份英语老师的工作实则就是为了一个稳定工作的证明,否则她没有办法拿到签证。
导游工作比学校更自由,赚的也多。她喜欢呆在这样有西式情调的餐厅里,即使不是和游客来,她自己偶尔也会来坐坐。
她很向往美国,希望通过旅游行业实现她的美国梦。我从她看那些贵妇的眼神中,能感受到她对那种生活的向往,但她知道她和他们不一样,但眼前欲望促使她一定要逃离这里,改变现在的样子。
越南:
去越南,是重返之旅。Sam三年前,在胡志明以南的城市偶遇的一位老师和学校。
当年他没有目的地开着摩托车在路上偶遇到了Mr.Tan,虽然Mr.Tan几乎不会几个英语单词,但他很热情好客地带他去了他的家和学校。当时他还给他们上了英语课,Sam说他很喜欢和这些小学生们聊天,虽然也都是很基本的对话,但他很开心。
自那以后,他心里种了一个草。可能的话,他想资助这个学校,还能再去看看这些学生。在这三年间,Mr.Tan也时常和他邮件往来,大部分是问他资助学校的意向。
Sam一直想说再去看看后再做决定,但Mr.Tan不知道是不是觉得没什么希望,渐渐不再有往来,邮件也不再回复了。
今年去之前,想联系他,也一直没有回复。直到我们再到那个学校所在的镇后,给他电话,他傻笑着问问,在哪来他来找我们。
Mr.Tan知道自己英语不好,那天还找来了学校的英语老师一起来见我们。见面后,Sam和我说Tan变了很多,那时见他还不抽烟,也不穿西装裤和衬衫,现在还提了个公文包,看上去生活好了很多。
听他们谈话中,三年前的学校还是在一个很落魄的环境中,现在的学校搬了新地方,这几年有越来越多国家的志愿者志愿者来学校参观和上课。他也添了手提电脑、平板电脑等数码设备给学生上课用。他还有些不熟悉的操作着这些电子设备,想翻阅照片给我们看。
聊了许久,Sam提出想去学校看看,Tan说今天下午他有课,一会儿就带我们去。
我想象中的学校再小,也是分了几个教室的。但这个所谓的“学校”,在我来看就是个托管所,或者好听些是个私塾。教室就在居民区里,相当于农村房子的一楼客厅腾出的空间当教室。学生也不分年纪,大家都坐在这个空间里。
貌似这个“学校”也没有上课时间,一些学生穿着便服来,一些学生穿着自己正式上课的校服来。我们大约10点多到后,就一直坐在椅子上,看着陆陆续续地孩子跑来,低年级的孩子很愿意聊天,高年级的孩子就安安静静地坐在边上。
大约到下午2点多时,Mr.Tan突然宣布上课了,他拿了一张纸递给我,傻笑着意思让我来上英语课。我一点准备也没有,但更我惊到的是,接到纸后,纸上就是两页的单词,分别写着越南发音和意思。
我临时划出了些简单的单词,比如,fine,like,work.想结合使用的生活中简单对话,能让小朋友们能开口说。
没想到他们英语对话比我想象的更糟,onetwothree的数字的吐音都不对,而他们能对话可以有的反应是howareyou,I’mfinethankyouandyou?Howoldareyou?Iam__yearsold.
当我鼓励他们模仿一下生活情节的对话,孩子们也都很不好意思开口,这我能理解他们的害羞,试图用游戏让大家活跃起来。课上的我汗流浃背之时,Tan依旧在一旁叼着烟,露着白牙傻笑着。
Sam一开始还配合和孩子们对话,但最后说,他们不这么上课,我来演示给你看。他用教棒敲击着黑板上的单词,大声朗读了一下,孩子们就本能反应的跟着朗读,重复两遍,进入下一个单词。
我有些恼火的表示,我们以前就这么上课,最后什么也记不住,也说不了。这样学不会语言。但Sam无奈地回应,他们就是这样上课,孩子们发音不标准,是因为老师就是这么发音的…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当我想询问这个学校的资质、性质之类,都不能给到回答,我尝试Google翻译成越南语,Mr.Tan看了看仍旧是傻笑…我很无语…
而据说这个“学校”是半公益性质,但父母也需要支付一定费用,而大部分学校都来自家境较好的家庭。只能希望这个“学校”不是被Mr.Tan利用赚钱的工具吧~
斯里兰卡:
今年是第二次去斯里兰卡,每提到这个地方,我总会浮现出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电影开头动物园画面,美好,和中年Pi在和书中的作者聊天的画面。
第一次去斯里兰卡遇到了向导Isuru,他好似电影中那个中年Pi,虽然没有Pi那么奇幻的故事,但生活也很不易。然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困境、奇迹,再他口中总是轻描淡写,对国家发生的政变,遭受的自然灾害,并没有哀怨和愤气。
Isuru曾去日本车行打工,但父亲突然病危,他回到家后,填上了是有多积蓄,但仍欠下了多万斯里兰卡币,当时由于回家突然,并不能找到理想稳定的工作,也是在那时,因为他会说日语和英语,所以做起了私人导游。
父亲重病那会儿,Isuru一直瞒着母亲,总说父亲的病一定要住院而已,父亲去世了一段时间,他也还了所有债,才让母亲知道。
现在他和他的夫人结婚大约也5、6年了,两人觉得过了适育的年龄,就不准备要孩子了,这在斯里兰卡也算是很前卫的家庭了。
“这是命运的轮回,总不会有一帆风顺的人生。但我相信因果善报,只要向着善的方向,那些劫都会有解。所以我觉得不善的事情绝不会做,希望有更多善良的人来到我生命里。”
去年见他那会儿,他已经赚钱开始规划自己的将来。这次又欠下好多钱,不过是为自己的喜好,他非常喜欢车,只要和车有关的东西,都会让他兴奋。所以他狠心贷款买了一辆日系的商务车,自己开的开心,客人也坐的舒服。
不仅有了“小老婆”,他也透露已经厌倦了旅行社安排的一尘不变那些“著名景点”和“购物团”,他打算自己想设计一些野营、观鸟等一些独一无二的路线和新地方,让游客和自己都有新鲜感和特色。他还打算着和朋友商量开家斯里兰卡特色餐厅,为以后不做导游后的生活做打算。
今年再见到他,人到时没有什么变化,但去年他说的那些打算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了。今年去之前,他还特地让我在淘宝上帮他选个望远镜,为了能在观鸟路线上用。
土耳其:
今年,不期而遇的在这个国家呆了近一个月的时间。
两年前,人们提到这个国家的第一反应是《花样姐姐》、《花儿与少年》、热气球。
而在此后的两年后,一提到土耳其确是恐袭、政变等的危险之地。曾看到在一个北京治疗白癜风大概要多少钱白癜风用药
转载请注明:http://www.xuefolanqc.com/zrzy/153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