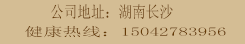一
还记不记得那个右手画圆,左手画方的游戏。
小学第一节美术课上老师神秘兮兮地把画得好的同学召集到讲台上站成一排,大声宣布这些同学是班里比较聪明的孩子,然后小脑协调啊平衡感的解释了一大堆。印象中大概是从那之后,我在和秦丹的友谊中就始终处在被动地位。
我为此很受伤却一直听天认命地相信我的平衡感真的不好,直到这一刻我才发现,这跟双手协调什么的根本没有关系,因为即使是单手画圆我仍然画得很糟糕。
但在这种情况下发现这一点绝对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儿。
我尴尬地望着自己在黑板上画下的只能说是很像圆的巨大图形,向后退了一步,侥幸地觉得如果隔远点看会好一点。在发现这样做完全没有效果后,我心怀忐忑地把目光转向在一旁看好戏的地理老师。她抱着胳膊,一副看好戏的样子从暗处走出来,用书戳着圆上最明显的一处凹陷讽刺道:“程遥,地球的什么地方好端端出来这么大一个坑?是地震了,还是海啸?”
我一声不吭地转身往座位走,心里默默预备着她的尖嗓音在背后突然响起,以免像前几次那样被吓一跳。我知道比起那个难看的圆,我的态度更让她恼火。
果然,我还没来得及坐下,她刻薄的声音就传了过来:“看看,你连地球都画不圆,还想画世界工业分布图?”
我才没想画,是你让我上去画的。
我不知道做值日的秦丹是故意没擦黑板还是像她说的那样真的忘记了,总之下节课数学老师进来的时候,那个丑陋的圆依然留在上面。好脾气的数学老师看了一眼黑板后乐呵呵地说:“谁这么好心啊,连这节课我们要复习的椭圆都帮我准备好了。”然后笑眯眯地把目光投向课代表。
“不不不,不是我。”数学课代表慌慌张张地站起来,拼命地摆手,一副急着撇清关系的样子。
难道那个圆就真画得这么对不起人,我郁闷地想。
那些缺陷被数学老师熟练补好的瞬间,我却莫名其妙地失落起来。
地球是圆的,真的那么好么?
记忆中中那些讲述离别的悲伤的电影画面,最后一个镜头都是一个人孤单地站在原地,微笑或是流着眼泪凝望着远去的火车、轮渡,或是简单的背影一点点变小,最后在地平线消失。
如果地球不是圆的的话,那么就不会有“地平线”这个词。
所以,也不会有“消失在地平线”这个句子。
小说里很多相隔很远而见不到面的亲人和爱人会互相安慰说:“至少我们在同一个地球上。”其实正是因为在这个滚圆滚圆的地球上,才会看不见的吧。只因为不在地球上,那么远的星星,我们都可以看得见。
如果地球不是圆的,那些走着奔跑着或是坐在车上离开我们的人,尽管会因为距离越来越远而一点点变小,甚至只剩一个小点,却永远不会在某个地方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
只要用力寻找,也许会看不清,但不会看不见。
这时数学老师冲着我的方向眨眨眼睛说:“椭圆不是一个普通的圆哦,它是个扁扁的圆。”全班都被逗笑了。
我把那截一直攥在手心里的粉笔塞进课桌里的罐子。
二
这个罐子是井留下来的。
井坐在我旁边的几个月里,它一直摆在我们的课桌中间。
井的梦想是环游世界,可能他的说法更文艺一些,但在我看来就是这个意思。
井书桌的抽屉里放满了成摞的旅游杂志,他刚坐在我旁边的时候因为和我不熟,只是每天一个人安静地在一旁翻杂志。后来的某一天他试探性地推了我一下说:“你看你看,这个地方我去过。”然后无视我一脸的诧异自顾自地讲起来。从此以后,他翻杂志的时候几乎是一刻不停地在讲话,开场白除了“你看你看,这个地方我去过”就是“你看你看,这个地方我没去过。”然后真诚地表白他有多么想去,说着说着就会牵强地引申到他环游世界的理想。
有一次他又在我耳朵旁边唠唠叨叨地说他一定要去世界的所有地方看一看的时候,我突然转过头看着他说:“我也是。”
他愣愣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接着像找到知己一样一脸激动:“真的吗?那我们可以一起攒钱了。”井开心的脸,让我很惭愧。但只有梦想,我倔强地不想输掉。
井喜欢校门口超市卖的一种做的很可爱,每盒有五种口味的口香糖。有一天他从外面捧了一个大罐子进来,兴奋地说那个口香糖换了包装,我装出不想理他的样子,却用余光惊异地看着他一天之内把它们全部吃光,好像就是从那之后井就总嚷嚷牙疼什么的。
然后井把那个罐子擦干净,放在我们桌子中间。我皱起眉头说:“你这是要干嘛?”
“这是旅游基金啊,”井笑着把罐子转过来,上面有一张写着“旅游基金”的纸条,“我们不是要一起去旅行吗,现在就开始攒钱吧,一分一分的。”然后郑重其事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硬币硬币塞进去。
那一瞬间,我有些感动的说不出话,却还是虚伪地挑刺道:“一分钱根本没用的好不好。”然后面无表情地拿过盒子,把那张纸一把撕下来。井一副快要哭了的样子看着我,我说:“你字太难看了,我重新写一张。”
其实井的字写得并不难看,反而像他讲中文一样好的让人没话说,以至于他在讲台上说自己是日本人的时候根本没有人相信他。后来听老师解释说,他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不停地转学,井去过许多国家和数不清的城市,这次来中国已经是第五次了。
我妈听说我旁边坐了一个日本小孩,叮咛我一定要把他领回家看一看。老师们也觉得稀罕得很,对井表现出毫不掩饰的偏心。语文老师有一次一副老不正经的样子凑到井旁边看了半天,张开嘴抖动半天秀出一个“CLEVER”。井还没来得及反应,我就忍不住“扑”得笑出来。老师的表情顿时变得严肃,脸上的皱纹拧到一起,很不满意得看着我。
崇洋媚外,崇洋媚外,崇洋媚外。
即使这样,井还是对我们的课程明显缺乏兴趣。尽管他的中文说得挺不错,但终究没有达到可以在语文课上应对像是挑错字,填成语这些刁钻古怪的高考题目的水准。井跟我一样虽然对数学老师胖胖的脸着迷,但对数学实在喜欢不起来。他去过许多国家,根本不屑和我们这些只会纸上谈兵的人一起背什么单词、造什么句子,所以英语课心安理得地趴在桌子上睡大觉。
而这样的井,却对地理课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地理老师自然受宠若惊,课与以前比起来讲得格外卖力,虽然感觉上是为井一个人讲的。后来她几乎是达到了讲一句就试着与井交换一次眼神的程度,井也乐意理她,眼睛瞪得大大的,不停地点头,班里其余人就这么无辜地被他们忽略掉了。井说地理老师的课讲得相当有意思,我说我听了这么多年怎么没听出来。
他说:“你看她每讲一个地方,都会描述那里的气候,介绍那里主要城市的特色,还有那里的平原啊山川的都会讲到。”
那有什么有意思的?
我无奈地解释说只要是地理老师都是这样讲的,因为这是高考大纲要求的。
他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绿色的本子在上面画来画去,每次我说话他听不懂的时候,就会在那个本子上比划。结果他比划了半天的结果就是抬起头一脸羡慕地看着我说:“你们的高考真有意思。”
这绝对是赤裸裸的挖苦。他一句话不知道伤害了广阔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多少人。
我说:“你到学校门口把这句话大声喊出来,你明天大概就来不了学校了。”然后无奈地看着他又在那个本子上比划。
对于井的离开,我是表现得最为惊奇的一个,但这种惊奇的程度也只是在那天早上走进教室看见井桌子上的书都不见了的时候愣了一会儿,然后淡淡“哦”了一声。
即使是那么稀罕的井,在走了以后,老师们也显得若无其事,仿佛这个人从来没有出现一样。只有地理老师,四周仿佛笼罩着重重的失落感,讲课时看起来很疲惫的样子,还经常把怒火迁移到我头上。秦丹说,大概是因为井让在她习惯了被学生冷落之后重新发现了自己的价值吧。
三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井那个罐子和天真的计划,我开始对硬币掉在地上的声音分外敏感。而且只要听见类似的声响,就会条件反射似的伸长脖子拼命往地上张望。有一次我在公交车上这样做了的时候,被我爸狠狠训斥了一顿,说我没出息。
可是哪里有那么多会把钱丢在地上的人,就算有,又有几个人丢了钱之后会大方到懒得去捡。看着井弯着腰在每张桌子下面认真搜索的样子,我就会暗暗后悔自己居然心头一热就加入了井这个丢脸的计划。
井每节课都把罐子里那几个可怜巴巴的硬币倒出来,愁眉苦脸反复地看,仿佛多看几遍就会增加一样。或者是在一边自娱自乐地对着自己的耳朵摇罐子,摇得霹雳啪啦响,自欺欺人地制造里面其实有不少钱的幻觉。
终于有一天井很严肃地说不能这样下去了,否则哪里也去不了。我们讨论了半天虚伪地良心发现这钱还是要我们两个亲自出才有意义。忘记是谁先提出一个这么笨的方法,另一个也好不到哪去的答应了。就是每天互相提问课本上的问题,答不出来的人就要自觉地放一枚硬币在里面。
我说那就背唐诗吧,井就又用那种快要哭出来的目光看着我。我说:“那怎么办,难不成做数学题,我可不要。”井也使劲点了点头,我想要是数学老师看到这一幕会是多么伤心。
井说,那就背地理地图吧。有那么多的国家,那么多的城市,还有那么多的平原、山脉和河流,记起来挺有意思的,顺便可以研究一下我们到底要去哪里玩。这样公平些,钱攒的也快些。我想着是啊,就答应了。
然后井很满足地笑了,然后说了一句让我想把自己的舌头咬掉的话。
“程遥你知道么,世界地图我全都背过了呢,每一座山脉,每一条河流,每一个岛屿,每一个被标记出来的城市,我全都背过了。”
钱的确攒的快些了,却一点也不公平。每答错一个问题虽然只要被罚一毛钱,却让我充分懂得了什么叫做“如果你现在瞧不起一毛钱,将来就会为一毛钱哭泣”。开始的一星期里,我疯狂地输钱,咬牙切齿地看着井把我从A那里换来的一把一把的一角钱硬币从罐子里倒出来,再找到A换回一元硬币来放回去。秦丹有一天终于受不了了气愤地回过头冲我们吼道:“你们俩幼不幼稚,多大了还拿一毛钱玩,我要调座位!”
那些日子我被逼到一下课就装肚子痛跑厕所,只为了逃避井心血来潮突然提出的像是伊希姆草原和巴拉巴草原之间的河流是什么之类的一大堆问题轰炸。当我又一次用几乎要把罐子拍扁的力量把硬币塞进那个罐子里的时候,恼羞成怒地问他老师什么时候讲过这些,他说:“地图啊,地图上都有。”我说:“不可能,我把世界地图都看了个遍。”他说:“哦,那就是亚洲地图吧,亚洲地图。”
有钱能使鬼推磨,为了不有朝一日把我们家都输光,我拼了命地背地图。我把学校发的地图册一页一页扯下来,又去书店淘了几卷地图抱回来,然后把大大小小的地图贴的满房间都是,以至于有一次秦丹去我们家进我房间的时候吓了一跳,她说我表情表情凶险地坐在一堆地图中央,看起来像要发动一场世界战争。
所以在井第一次垂头丧气地投钱进去的时候,我感到从未有过的骄傲。
我开始渐渐喜欢上井那些铺满风景的旅行杂志,里面的绚丽的色彩和诱人的文字,让我对那些美丽地方的向往越来越真实而不仅仅来自井攀比梦想的逞强。我们会在每天放学后把它们摊开,周围的桌子上摆得乱七八糟,每天讨论着到底去哪里比较好,或是仅仅争论像是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哪个看起来比较有感觉这样的问题。
“中国好玩的地方有哪些啊?”井一脸期待地看着我。
“其实城市跟城市都差不多,漂亮的地方都很远的,像是……”我自信知道的地方有很多,但当时脑子却一片空白,“像是九寨沟啊,布达拉宫、黄山,还有……还有东方乐园什么的。”我硬着头皮瞎掰,责怪自己真是给祖国丢脸。
“东方乐园不是火车站附近那个地方吗?”
他知道得还真多。
第二天早上我进教室的时候,看见井低着头很别扭地坐在那里。
“程遥。”我坐下的时候,他小声叫我。
“干什么?”我转过脸看他,发现他居然脸红了。
“你是不是想约我出去玩?”
“什么?”我眼睛睁得老大。
“秦丹说的,秦丹说你故意提到东方乐园,就是暗示我想和我一起去那里玩。”
那个时候我没有意识到的是,就像东方乐园绝对不会在世界地图甚至是中国地图上被标识出来一样,每个人看世界的目光也像绘制不同大小的地图一样有着不同大小的比例尺。
我们要一起去看整个世界,那什么是整个世界呢?对一只蚂蚁来说,一棵大树就是它的全世界;对一只兔子来说,整个森里就是它的全世界。它们梦想重合的部分,不过是因为偶尔在那棵树下遇见而已。
我能够走的距离,在井看来,也许近似原地踏步。
有一次我看见我妈在做饭就心血来潮地跑过去对她说:“妈,我想出去玩,给我点钱吧。”
“去哪玩?”她头也不抬地把黄瓜切片。
“西藏吧,丽江也行。”我满怀期待地说。
“去那么远干什么,星期天找个公园玩玩就行了。”
我叹了口气,想着我们果然是母女。
四
罐子里的钱多到每天都可以让我们花整整两节课去数,虽然这其中也有我们俩都笨手笨脚的原因。两个人数着数着就会混到一起,要不就是突然忘记数到哪里了,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会气急败坏地那堆硬币往旁边一推,而井却总是接过来继续一枚一枚耐心地数。他认真的样子,好看的让我有些感动。
有一次我看见他很满意地笑了,就忍不住把脸凑过去问:“有多少钱了?”
“138块7毛,”他笑着看我,“挺多吧。”
“挺多。”至少比我想象得多,我微微有些吃惊。
“那够去哪里玩了?布达拉宫?还有你上次说的什么山……”
“够在东方乐园不吃不喝玩一天了。”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本来以为会看到他沮丧的表情,但意外地看见他眼睛里全是意味深长的笑意,顿时明白他又误会我什么了。
那天下午我和井抱着那个罐子翘课跑到学校门口。
“东方乐园往哪走?”我随口问了一句,发现他居然吃惊地看着我。几秒钟后他干巴巴地开口:“你不知道吗?”
“我怎么会知道?”这个游乐场是前两年刚建的,我只是听说但从来没去过,哪个高中生会有心情去什么游乐场。我气急败坏地瞪着井说,“难道你也不知道?”
井很不可思议地看着我说:“你在这里住了这么多年都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知道呢?”
井在口舌上从来占不了便宜,但他这句话确实让我无话可说。我只是直觉性地认为,井认识世界上的所有地方,包括怎样到达。
给秦丹打电话纯粹属于病急乱投医,我早就应该料到她比我强不到哪里去,她支支吾吾半天说:“东方乐园肯定是在东边啊。”然后干脆利落地挂断了电话。
“哪边是东?”我和井几乎同时问道,然后怒视对方。
上星期我爸挥舞着我一模考试不及格的数学试卷,充满感情地奚落道,每天吹牛要考第一的人,连几个数学公式都记不住的时候。我不知怎么就突然想起这件事,也在心里讥讽道,两个每天计划着要走遍全世界的人,连哪边是东都搞不清楚。
看来我缺少的不只是平衡感,连方向感也很差。
连方向都分不清楚的人,还想去多远的地方?就算一直走一直走,最后的结果,可能也只是迷路而已。
只能说我们俩果然像秦丹说得一样,幼稚得很。
秦丹的数学也考砸了,她无理取闹地说都是因为我在几个月前的数学课老师讲到重要地方的时候打电话给她问路。然后指着我的鼻子说我简直是莫名其妙。
这是我要说的才对……我无奈地想。
“有那么多人,为什么偏偏打电话给我?”她还在那里喋喋不休。
“因为你平衡感比较好。”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她愤怒地回过头不再理我。
也许,会把我莫名其妙的话傻乎乎地抄在在本子上不停地比划直到想明白的人,真的只有井而已。
五
如果真的有人来问我东边的话,我也不见得答不出来。
我可以告诉他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东边是华盛顿,孟加拉湾的东边是安达曼海,东非大裂谷东边是维多利亚湖,我想我可以指出地球上任何地方的方向,除了这里。
就像很多人总觉得可以把那些离他们远之又远的东西看得清清楚楚,却无法看清清现在。
而我真正想知道的,却只有现在。
六
我发现井经常从钱包里拿出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便签纸,很认真地默背一会儿,再小心翼翼地放回去。
有一次井说错答案后想抵赖,我抢他钱包的时候那张纸从里面掉出来,井立刻宝贝似的捡起来。我说我想看看,他犹豫了一会儿递过来,一脸心疼地说那是很重要的东西,千万别弄坏了。
我接过来展开一看,除了最上面一行的中文,全是密密麻麻我不认识的字符。“这是什么?”我问。
井说那是被翻译成很多种语言的自我介绍,“很厉害吧。”他得意地说。
“你们好,我的名字是井,来自日本,很高兴认识你们,希望我们可以成为朋友。”我一字一顿地念出来。“井”字上还认真地标了声调,我觉得好笑却一点也笑不出来。
井说他第一次在讲台上背这句中文的时候,尽管字数不多并且之前练习过,但还是讲的磕磕绊绊,好几次咬到自己的舌头,最后没有说完就红着脸跑下去了。
井说他每到一个地方,都随时准备着离开。所以那份被小心保存在钱包里的自我介绍随时准备被取出来。
“离开”这个词似乎无论怎样表达都带着挥之不去的悲伤和寂寞,却被井讲得兴高采烈、斗志昂扬。我自讨没趣投向他的同情的目光只好悻悻地缩回来落在自己身上。
井永远对下一次的出发迫不及待。印象中那些不断行走在旅途中的人,应该是充满乡愁,并且梦想着可以有一天可以停下来不再漂泊,拥有一个可以让自己安心的家。他们忧伤落寞的脸让人看了有说不出的心疼,而看着井亢奋的表情只想让人给他一拳。
拿到那张不及格的地理试卷的时候,我第一次庆幸还好井走了,否则一定会在他面前抬不起头。
那个地理考了第一的男生被地理老师推上去形式性地介绍经验,他就像小学生端着奖状一样捏着自己的试卷说:“其实把地理学好很简单的,买一张世界地图多看看就可以了。”羞涩却掩饰不住的得意。
我不屑地发出“哼”的声音,心里却觉很不是滋味。
世界地图上每一个国家的名字,每一座岛屿的名字,每一条山脉的名字,每一片平原的名字,我都可以一字不错地说出来。
我知道这么多这么多的地方,却不知道现在井在哪里。
“程瑶,那你来说说……”地理老师的声音总是没有前兆地响起来。
我叹了口气慢吞吞地站起来,看着她指着美国东部的那条山脉。
“这是哪里?”
“阿巴拉契亚山脉,阿巴拉契亚山脉。”秦丹回过头用书遮住嘴说。
“我不知道。”
地理老师总找我麻烦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也发现了自己似乎总在地理课上表现出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其实我不是故意的。
那些地理老师在黑板上圈出来的,名字对我来说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地方,现在看上去是那么刺眼。我不是井,我越渴望的目光只能被它们还以更尖利嘲笑。比起它们胜利的笑容,地理老师的笑容要相对的好看那么一点。
幼稚地想要去看世界的其实只有我一个人。
告诉井底下的青蛙天空并不是像碗一样大,而且很美丽很漂亮有什么意义么?就像你向一个没有双腿的人描述奔跑的快乐,传递给他的也只是虚伪的美妙和继之而来的无力感。某种意义上说,和欺骗在形式上完全没有区别。
“程遥,那你来说说……”
“程遥,那你来画画……”
仿佛在不停地地逼我提醒自己,那些地方,你是绝对到不了的。
而这一点,我是知道的。
我想起那节地理课上我在地球上画出的巨大的坑洞,那个地方可能真的存在的,大概就在我脚下。
没有地震也没有海啸,只是安静地存在着。
七
只要教室门口有一点动静,我就会忍不住抬头张望。
我总觉得井会在某一天突然出现在教室门口,大声叫我的名字,说他忘记把他的“旅游基金”带走了。
后来我做了一个梦,梦里井微笑着走近我,然后高高举起那个罐子,把所有的硬币哗啦啦倒在我面前,转身走的时候说:“我才不稀罕。”
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趴在桌子上,手臂底下的书已经湿了。我打开罐子,发现硬币还在后松了口气,然后觉得自己真的挺没出息的。
我没有提名字地告诉秦丹我梦见有人把东西摔在我脸上,所以觉得很伤心。
秦丹难得好心地安慰我说:“别多想,梦都是反的。”
我刚要感动地拥抱她时,她又接着说:“所以应该是你把东西摔在他脸上。”
前几天有个男生转学去北京,班里为他开了送行会。他站在讲台上抹着眼泪说着“同学们我一定不会忘记你们”的时候,秦丹小声对我说:“我哪天要是走了绝对不会像他那样,我一定会走得很潇洒。等你们发现我不见了的时候,我的书桌,鞋柜,宿舍里的床铺,所有的东西早已经全空了。”
她在说这些话的表情好像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在桌子下面悄悄握紧了拳头
原来那时你也是这样得意啊。
这样看来,也许我真的会找点什么摔在他们脸上也说不定。
但比起生气,我更多的是沮丧。
想到井兴高采烈地背着书包走进某个教室熟练地背诵他的自我介绍;想到井开心地对着什么人说着他到过的地方遇见过的人,想象着那个某人在听到这个城市或是我的名字的时候一脸不耐烦的样子,我就会沮丧地一塌糊涂。
不过这样说来,井讲起他想去的地方的热情永远高于描述那些他去过的地方。而且也很少听他提起以前交的朋友,只是经常看见他从外面跑回来开心地对我说他又认识了哪个班的某某某。
井属于这样一种人,适合他们的台词永远是:“我又认识了一个人。”
而属于我的台词是:“又一个人离开了我。”
对井来说,无论多少次,硬币是可以重新一枚一枚攒起来的吧。
我这样想着,硬币不小心从手里滚出来掉到地上。
我拍拍坐在前面的秦丹,拜托她帮忙把钱捡起来。
秦丹点点头弯下腰去,然后用极慢的速度直起身子,翘着兰花指阴阳怪气地问我:“同学,你刚才掉钱了吗。”
“嗯。”我不太想理她,所以尽量减少和她交流的字数。
“那么你掉的是一块钱还是一百块。”她哆哆嗦嗦的,看起来有点恶心。
“一百块。”我没好气地说。
“你不诚实,”她诡异地笑了,“所以不能还给你。”然后把钱揣进自己的口袋,没事儿似的转回去。
“我才不稀罕。”我小声地说。
八
地理测试有一道题是这样的:有一个人从北半球的回归线上出发,他先向东走了1000千米,再向南走了1000千米,又向西走了1000千米,最后向北走了1000千米。问题是:他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哪里?
那时候我毫不犹豫地选了“回到原点”,试卷发下来后发现被打了大大的错号难以置信地睁大了眼睛。但当时没有认真听老师讲,自己也没有好好想过。
不过,现在好像有那么一点明白了。
是不是说如果你离开了原来的世界,那么即使你沿着来时的方向往回走同样的距离,可能也回不到原来的地方。
所以回不到过去的,不一定都是时间。
我把“旅游基金”全部取出来,周末一个人怀着一种报复心理在东方乐园玩了整整一天,并且用井的那份钱大吃大喝。
谁说回忆的价值无法计算。我和井的回忆刚刚好值三个汉堡、七只鸡腿、三份薯条、两杯可乐和一支冰淇淋。
结果我发现我连坐车的钱也没剩下,只能边在心里骂井怎么数的钱,一边狼狈地走回去。
路面和天空被各种颜色的灯光照得通透,甚至比白天还要耀眼,让人几乎忘记黑夜的事实。就像是那些铺在记忆上方闪着光芒的地图和风景照片,把我脚下那个巨大的坑洞温柔的隐藏起来,那些瞬间我是真心觉得自己仿佛可以像井一样,旅行也好,逃避也好,寻找也好,总之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却忘记了自己甚至连一小步都无法跨出。
就算走得很远,也害怕像现在这样会找不到回去的路。
有时我会想,如果从来没有遇见井的话会不会真的比较好,我会一直安心地沉睡在这个城市,对平静而琐碎的生活满足并感到温暖,为缺少平衡感这样的问题感到沮丧,从来不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可是因为井,我开始拼命地想看清楚那些离我很远很远的东西,并且不知不觉中开始痴迷,我是那么喜欢它们,以至于到现在不忍心承认它们其实不切实际。
沿着同样的方向往回走,都不一定可以回到原来的地方。所以因为井偏离了的世界,并不能简单地因为井的离开而天真烂漫地回到原点。
甚至还没有出发,就已经回不去了。
那种雀跃着的,无法按耐的心情到现在依然那么真实的存在着。
因为知道了天空不是像碗一样大,因为知道了天空很漂亮很美丽,所以水井下面的青蛙有了到外面世界去的梦想。
我依然想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这种想要奔跑的冲动,也许,不仅仅是逃避而已。
第二天的地理课,我把揉成一团的试卷重新展开,对着答案一道题一道题得改正,答错的和故意没答的。
“那程遥你来说说……这是哪里?”地理老师笑着指指黑板。
“密克罗尼西亚群岛。”我说。
她似乎已经准备好了我的沉默,讽刺我的话刚要说出口就被生生噎了回去,气氛顿时有些尴尬。
我没有坐下,而是站着继续说:“您指的那一部分也可能是里面的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吉尔伯特群岛、巴纳巴岛、瑙鲁岛……”
“从那边延伸过去是新几内亚岛、所罗门群岛、图瓦卢群岛、萨摩拉群岛、库克群岛、社会群岛、甘比尔岛……”我这样说着的时候,眼泪不停地流出来,我甚至尽量不去呼吸,生怕一停下来,就无法继续下去。
好久都没有说起这些地方了,我还以为我会忘记。
不过,还好没有忘记。
如果可以看得很远很远,那么看不清现在又怎么样呢?
如果可以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就算不知道现在在哪里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只要知道自己想去的地方就可以了。
也许就像那道题目说的那样,我走不回去了。但也许,我是更靠近了自己想去的地方。
那些从我唇齿间以极快的节奏跳跃出来的名字,像极了那个梦里被哗啦啦地倾撒出来的硬币。
像极了,在我周围渐渐清晰起来的掌声。
因为我不是井,所以我会把它们一个一个地捡起来。
赞赏
转载请注明:http://www.xuefolanqc.com/rkzz/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