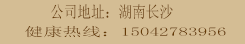![]() 当前位置: 库克群岛 > 国家象征 > 太远的一步双重文化主义AStept
当前位置: 库克群岛 > 国家象征 > 太远的一步双重文化主义AStept

![]() 当前位置: 库克群岛 > 国家象征 > 太远的一步双重文化主义AStept
当前位置: 库克群岛 > 国家象征 > 太远的一步双重文化主义AStept
太过分的一步:二元文化主义
原文作者:RossMeurant
翻译:EverestPanm
双重文化主义
《二元文化主义》正如其字面所言并加上其散布者依据的“伙伴关系”概念,想要毛利人应以平等的伙伴的身份统治新西兰,与我们的“其他”新西兰人一样。
通过其详细的描述,二元文化主义在新西兰如今却显现为:分裂。
什么是“伙伴关系”?
《怀唐伊条约》的规定就它在宪法上的概念而言,在政治面上丰富经验的政客如戴维·兰格阁下、比尔·英格里希爵士和温斯顿·彼得斯阁下等具有都驳回所谓该条约创造了“毛利人与王室之间的伙伴关系”这一主张。
在政治界和伪学术界,总检察长兼负责条约谈判的部长克里斯·芬利森(ChrisFinlayson)以及因对毛利人的愿望深表同情而闻名的某人表示“毫无疑问,王室在新西兰拥有主权”。(1)
在学术层面上,前法官兼法律讲师安东尼·威利(AnthonyWilly)通过某些毛利要素全面提供了三方面原因,说明合伙制是没有根据的。
与这次辩论特别相关的是,他解释说自从年毛利委员会法院上诉一案中使用“伙伴关系”一词以来,所谓激进分子声称这是他们与官方存在“伙伴关系”的证据只是审理中评论的一部分而不是决定。这个概念没有法律依据。(2)
穆里尔·纽曼博士(DrMurielNewman)辩称:某些毛利内部元素同时提出的“条约伙伴关系主张”是毫无根据的,是对正在被刺穿的新西兰民主的一个“大谎言”。(3)
但是,这个误导的理念所谓条约确实建立了治理伙伴关系已经被武器化了。它不再只是自我吹嘘的“影响者”手中的便利工具,而是在寻求计划我们的未来的“效颦”政客手中的危险武器。
在某些情况下,毛利人和其他人以这种虚假的法律借口散播所谓毛利人与新西兰主权国家之间的平等伙伴关系。这些人可能并不了解法律现实。但是在我看来在某些情况下,这是他们一种策略去尽可能地洗脑而且必要时威吓那些捍卫法律现实的人,现实是王室从未将任何主权割让给毛利人。
值得注意的是,海伦·克拉克阁下在任总理时,她称毛利人至上主义者为“仇恨与破坏者”,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4)
RossMeurant
什么是文化?
文化抓住了人们所感受到的这些本质A)以民俗,家庭传统和习俗的形式;B)以舞蹈和音乐的形式;C)信仰形式:宗教或信仰;D)代代传承的历史事件;E)语言是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对寻求保留其文化的种族群体表示同情。
新西兰统计局表示只有六分之一的毛利人能够说流利的毛利语。由于毛利人仅占我们总人口的六分之一,这就可能意味着我们总人口中只有约3%的人能够讲流利的毛利语。
对于某些人来说,保留毛利语很重要。但是要把复活毛利语作为义务来强加,更糟的是要作为义务强制非毛利人的族群体遵守?我认为这是太过分的一步了。
在我看来,这取决于毛利人来在新西兰保存自己文化,就像南岛的苏格兰后裔和北岛的达尔马提亚(Dalmatia)的后裔一样。
我从没有听说中国或印度社区要求将其语言强加于其他新西兰人-但是这两种文化都在蓬勃发展,并且就临界的人口规模而言他们的人口爆发增长是明显的,他们两者未来都将成为主要人口基础。
那么,新西兰的文化是什么?是跳高地舞吗?-就像我当年长大的时候?是哈卡吗?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橄榄球?
很多时候从俏皮话里道出了个真理念-让我们反思一下:新西兰的文化是什么?除了橄榄球和哈卡舞以外,我几乎看不到其他任何元素在新西兰新兴文化中。也许是类似于巴里·克鲁普(BarryCrump)的“好人”的怀旧特征;或者是穆雷·鲍尔(MurrayBall)的“烂平底鞋”?或许在什么地方的羊毛剪棚?
但是没有像莎士比亚,华兹华斯或拜伦阁下以及其他隐含在英国文化中的人。我也看不出任何与天鹅湖相当的东西。柴可夫斯基、鲍罗丁或肖斯塔科维奇–这些都是促成俄罗斯文化的元素,我在过去的20年中广泛接触了这些元素。
我们确实有在国际上受到称赞“我们的”DameKiriTeKanawa夫人。然而很难在崛起中综合形成的新西兰文化找到她的魅力。例如:她如何与科林·米德斯爵士(SirColinMeads)一起评价新西兰人?
定义“新西兰文化”可能尚未确定,但无论如何,把我国的文化割裂为“毛利文化”和“其它”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问题。
RossMeurant
我是谁?
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有必要明确我是混血儿更恰当(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其中有一部分是毛利血统,更多的是可证明的皇室血统。
在母亲的母系这边,我有爱尔兰血统和英国血统;在她的父亲的父系这边是挪威血统和毛利血统。
19世纪末,一些斯堪的纳维亚海员在霍基昂加跳上船。嘿嘿叫是联系,其余无需进一步说明。
在我父亲的母亲这边;我有苏格兰血统,还有他的父亲那边,法国血统和毛利人血统。
通过这个血统书,我可以说我的法国祖祖父在年悄然抵达卡菲亚(Kawhia),在那里他娶了毛利Tainui公主Kenehuru。
NgaMahuta酋长TeTuhi-O-Terangi的女儿,TeWherowhero国王的直接后裔。
也许你可以叫我,酋长?
还应该及时告知,我的第一任妻子的母亲是库克岛人和澳大利亚人的混血。因此,对于那些会以“反毛利人和种族主义者”的潮水袭击我的人:踩踏我轻一点因为这样做是践踏我亲属的梦想。
被迫接受二元文化主义,有以后对毛利人产生不满风险。
政府和主流媒体的压力下,去要求接受双重文化体制统治新西兰的多元文化的社会,很有可能导致“反冲”(5)。
例如:在我们的MMP体系下,华人政党可能会在我们议会内崛起,从而导致意想不到的政治结果吗?
是否一个新的政党建立在印度文化,还有泰国文化或菲律宾文化的基础上引入代表多元文化利益的不同政党,会提供一种手段来保护可能在双重文化体系下沦为“其余”的社区的价值观。
在政治上一贯和特别的是:“要小心自己想要的东西。”
二元文化主义显然旨在将毛利人提升到其他新西兰人之上,而多元文化正如其名样是包容的。
每种文化都必须有权保留自己的起源、自己的宗教、自己的语言和拥护自己的种族。任何文化都不应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多元文化主义=公平与公正。
让我们看一下到达新西兰的时间顺序。
毛利人最早在公元年左右到达新西兰。库佩当时是伟大的探险家。然而,Morori坚持认为,毛利人并不是第一个踏上这个对拓点前哨的人。
俄罗斯捕鲸者也曾经早早抵达岛屿湾。
法国殖民者曾在Banks半岛宿营。
苏格兰,英格兰,威尔士人来自“楼下”,是最早铺路到新西兰的白人移民。
华人在科罗曼德(Coromandel)和奥塔哥(Otago)的金矿中出现了,在那里他们受到了可恶的对待。一百年后,这些苦力已经从被排斥的下层阶级升级为企业主。
达尔马提亚人在20世纪初涌向北岛,在那里他们收获的Kauri树胶获得了比黄金出口更多的出口收入!
半个世纪以后;这些被称做“Dallies”的达尔马提亚人后代仍被种族歧视。然而今天,这些努力工作的移民的后代可能被发现已然是葡萄酒业、商业捕鱼业和建筑业的主要业主。
以彼得·塔利爵士为例。伊万·彼得·塔利扬基奇(IvanPeterTalijancich)的儿子(后称伊万·塔利),从莫图伊卡(Motueka)卑微地起家,最初是一家海鲜生产商。这个家庭几十年来在沿海拖网渔船上历经汹涌海浪创出一条生路,如今已成为地球上最大的鱼类出口商之一。后来延申至冷冻蔬菜,Affco肉类出口和旅馆业务。
年代中期,来自荷兰的人占据了统计数据的主导地位。今天在我们的奶业养殖部门中荷兰移民已然确立了他们的传奇。
来自欧洲各地的来港定居人士:法国人、德国人、波兰人、匈牙利人、瑞典人或丹麦人–不胜枚举。今天,它们为新西兰人口的多样性做出了贡献。
印度移民从六十年代开始进入。许多人在奥克兰南部建立了蔬菜种植农场,如今他们的后代繁衍起来。
到年代,太平洋岛国开始了移民。他们来自萨摩亚,库克群岛,汤加,纽埃和斐济。
新西兰形形色色的太平洋岛民社区是多元文化现象的另一种体现。
如果我可以用点时间谈谈“岛民”,就像七十年代所提到的那样。
作为70年代的一名警察侦探,刚来的岛人常被指责为棕色人种反社会行为的替罪羊,不管他们是不是肇事者。
不仅在警察中而且在许多新西兰人中,公然的种族主义情绪都撒在岛民身上。
事实是太平洋岛民带来了强大的家庭、宗教和辛勤工作的守则。
许多人从事体力劳动。他们努力工作为子女提供更好的生活起点。
我想起了新西兰橄榄球联盟前代表和前警官JoshLiava’a,在过去的五年中,我曾与他一起创办了一家私人保安公司,我们是伙伴并仍然在为警察服务。
Josh的目标是赚更多的钱来让自己的孩子读大学-他确实做到了。他出生于汤加,也是最早移民新西兰之一。
在这些年中,Josh实际上拥有三份工作!一名警察-他获得了警官警衔;一家私人保安公司的老板,我们也都在业余时间上大学:乔希(Josh)毕业于犯罪学专业。
最重要的是,他为新西兰踢了橄榄球联盟。
乔希即使不是第一个也是六十年代最早到达新西兰的太平洋岛民之一,他为许多其他人树立了标杆去追赶。
如今,具有太平洋岛背景的职业体育人士有趋势主导在橄榄球和联赛中新西兰的选择。
瓦莱丽·亚当斯阁下(DameValerieAdams)作为一位杰出的世界和奥林匹克冠军出类拔萃–她出生于的新西兰,父母是汤加人和英国人。
太平洋岛民的成功并不局限于运动场。在学术界,他们正在留下自己的印记。
如果我可以再回到以前的时光谈谈红队(RedSquad)。
受训红团警察的背景可以描述为;欧洲裔,毛利人和太平洋岛人。只有一个上过私立学校。当时,RedGroup没有亚洲或亚裔警察。
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
在我的警队中70%是欧洲裔,只有那个上个私立学校的小伙子后来毕业了法学学士。他也被委任。
两名第一代萨摩亚警察不是从富裕的家庭出来,仅占我警队队的10%,后来都毕业于法学学士学位和文学学士学位并且都被委任。
我警队有15%的毛利人;没有一个大学毕业,无人被委任。
以上的例子和比较中含有一个什么样信息?太平洋岛人他们克服偏见并往往在经济较低微的社区开始起步,在体育和学术界取得了高水平的成就-他们的成就率在人口占比高于这些领域奋斗中那些毛利人吗?
也许是时候新西兰要审视内在的问题了。
太平洋岛民群体保留了其母语、牢固的家庭联系和宗教信仰,而没有请愿政府将其文化强加于新西兰的其他文化群体。
太平洋岛民根深蒂固的文化价值观与毛利人之不同,就像萨摩亚传统文化与汤加的或斐济的差距一样。把他们归类为所谓“其他”既是侮辱也是冒犯。
双重文化伙伴关系模式迫使这些人抛弃他们真正的文化。要么在毛利人文化的一边,要么在其他文化的一边。
如果太平洋岛人民能够克服六十年代开始的大多数移民所面临的逆境-他们并没有保留地和毕业的优惠特权,也许是时候让新西兰和毛利人面对一些现实问题:为什么太多的毛利人萎缩到社会经济范例的近底端了?
正如柏拉图所说:“我们可以轻易原谅一个害怕黑暗的孩子。人生的真正悲剧是当人们害怕光明的时候。”
很多人做到了。
两位前国会议员与我有良好的关系,他们是得到我最高和持久的敬意的人做到了。在我进入国会初期的那段时间里,他们俩都支持我。那时有一段时间对我来说,很多事情挺棘手的。
彼得·塔普塞尔博士(HonSirDrPeterTapsel)和沙利文·瓦图·蒂里卡特尼爵士(HonWhetuTirikatene–Sullivan)。他们俩都是有杰出成就都是毛利人。
毛利人为新西兰军方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质兵员,现在仍然是如此。
我的兄弟布拉德·穆兰特(BradMeurant)和我出生在北岛农村,家境并不宽裕。我们本有足够的毛利人血统书去索取毛利人各种形式的补助金和援助。我们没有去。无形之中我们打破了所谓“童年劣势模式”,而一些做不到的毛利人经常以这个模式为失败找借口。
从一名自雇的水管工开始,布拉德在从事体育运动做到了。他曾经担任北港和酋长(NorthHarbourChief)的橄榄球教练和北部毛利橄榄球教练。也曾在南非,爱尔兰和日本担任过省级队的教练,并曾指导过格鲁吉亚国家队。最终成为北港橄榄球联盟主席。
我本人从一个不安稳的童年和没有拿到学校证书开始,可我现在拥有一个硕士学位两个半大学学位;任期9年的国会议员;曾任警察检查官(接手过名誉不佳的红队这个曾经的烫手山芋);目前为非洲国家名誉领事;俄罗斯在纽西兰拥有的大量商业资产的受托人兼首席执行官,并拥有我自己的国际商业利益。
我的人生旅程还包括在五十多岁时患了严重的12个月抑郁(男性不常见),这是那次Scampi事件引发的,见以下链接;
转载请注明:http://www.xuefolanqc.com/gjxz/654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