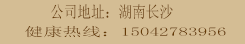![]() 当前位置: 库克群岛 > 国家气候 > 风之路南岛语族的原乡之旅
当前位置: 库克群岛 > 国家气候 > 风之路南岛语族的原乡之旅

![]() 当前位置: 库克群岛 > 国家气候 > 风之路南岛语族的原乡之旅
当前位置: 库克群岛 > 国家气候 > 风之路南岛语族的原乡之旅
一
年11月19日凌晨,一艘造型独特的独木舟正在缓缓地靠岸。午夜的闽江夜色深沉,马尾港像宽阔的广场,漫天的繁星犹如无数双眼睛在黑暗中凝视。一群人在岸上等候已久。桅杆上微弱的灯光姗姗来迟,10面国旗在晚风中猎猎作响。岸上的人开始欢呼,6名船员的面孔渐渐清晰起来。他们开始分工合作,熟练地朝岸上抛出绳索,将船固定在码头上,相互之间配合得十分默契。
这6名外国男子个个晒得黝黑,长发披肩,满脸胡须,看样子已经在海上航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有好几个月没有理发、剃胡子了,身上还散发着一股扑面而来的鱼腥味。不可思议的是,其中一个帅气的高个子张嘴就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我们4个月前走的时候,很多人以为我们到不了,说那个船肯定会沉下去。我们经过了10个国家,终于到了中国,真的是回家了。”
我们注意到,独木舟的船身上画着富有民族特色的鱼形花纹,“寻根之路”4个汉字显得格外醒目。这几个外国人为何寻根寻到了中国?他们是谁?福州又是怎样成为他们远方的家呢?
“年7月27日,晴。今天是‘寻根之路’的独木舟启程的日子。恰逢满月,在漫漫征程的初始给了我们一个吉祥之兆。17点整,在接受了大家的真诚祝愿和祈福之后,‘寻根之路’的独木舟在数十条船只的陪同下离开海口,驶入茫茫大海。”
在写下这篇日记后,5名法属波利尼西亚的南岛语族后人,从南太平洋的大溪地出发,沿着祖先年前的迁徙路线,反其道而行,经过海里的航程,途经库克群岛(库克群岛的山姆王子成了船上的第6个人)、纽埃、汤加、斐济、瓦努阿图、圣克鲁斯群岛、所罗门群岛、巴布亚新几内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回到了祖先当年出发的地方——中国福州。
茫茫大海充满了神秘和诱惑,稍有不慎就会葬身大海,注定了原乡之旅充满了艰险和挑战。南岛语族的探险家们试图还原年前的迁徙现场,以唤醒沉睡在体内的祖先。他们祈求祖先在天之灵,保佑他们一帆风顺。他们根据年的图纸制造了一艘长15米、宽1.6米的独木舟,不借助人工动力,主要依靠风帆的力量航行。他们用海水洗澡,靠捕鱼为生,生鱼片都吃怕了。有一次船舷进了水,他们连续几小时一桶一桶地把水舀出去,还有一次遇到了鲸鱼的跟踪……他们6个人挤在3平方米的船舱里,遭遇过台风和8米高的巨浪,恐惧和噩梦一路相随。他们说,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体验祖先的壮举和艰辛。
此次寻根活动的发起人叫易立亚,是人类学博士,曾在中国待过十多年时间,并娶了一位上海姑娘为妻,担任过法属波利尼西亚前总统外交顾问,所以说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出生于一个考古世家,寻根是他从小的梦想。为了此次航行,他毅然辞去了工作,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寻根计划中来。
南岛语族的归航,没有现代化的导航仪,甚至连古代的罗盘和指南针也没有安装。他们在海上是如何定位和识别方向的呢?易立亚说,因为船上有一双“航行的眼睛”。他就是有35年航海经验的老水手郭诺努伊。郭诺努伊采用的是一种被遗忘的方式,他白天看太阳,晚上观星象,同时辅助洋流和季风来判断方向,根据海水的盐分和鸟类的飞行估计距离陆地的远近。4个多月的漂流,独木舟始终没有偏离航向,事实证明郭诺努伊确实有一双好眼睛。
易立亚一行在福州参观了他们祖先曾生活过的地方——闽侯昙石山和平潭壳丘头两处史前遗址。易立亚说:“我们一直在找我们的根,我们的根就在这里。我们乘独木舟从波利尼西亚来到这里,足以证明独木舟是可以横跨太平洋的,当时的独木舟可以把我的祖先从这里带到太平洋上的任何一个岛屿。”老船长布努阿情不自禁地拿起吉他,用波利尼西亚语唱起了他在海上写的歌:“经过了多少大风、大浪、暴风雨,我们一路上跟着一颗星星来到中国……”
停泊在马尾港的独木舟,像飘落在水面上的一片叶子。它漂洋过海,不远万里,穿越半个地球,只为寻根问祖、叶落归根。在昙石山遗址的欢迎仪式上,法属波利尼西亚议长特马鲁语出惊人:“各位的祖先就是我们的祖先!”在壳丘头遗址上,南岛语族的后人们种下了一棵树,一棵生长着乡愁的树。不久之后,船员们将回到他们生活的岛屿,而这棵树将代替他们站在先人的故土上,为他们守望这早已失落的家园。中华上下五千年,年前,他们才是地地道道的福建人。
二
寻根之路的起点大溪地,首先让我想起了法国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笔下散发着太阳般光彩的大溪地少女。年,43岁的高更为了寻找欧洲文明丧失的淳朴和自然,独自一人来到蛮荒的大溪地。大溪地的美丽和神秘使他着迷,他不但与土著人共同生活,还娶了13岁的毛利女孩为妻。每次看到高更的油画,我总觉得那些赤裸上身的女人无论长相、肤色还是体形,都和中国人颇有几分相似。
大溪地位于新西兰和南美洲之间、夏威夷以南,因其秀丽的热带风光和色彩斑斓的海水,被称为“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地球上最后的伊甸园”。那里的居民衣食无忧,与世无争,他们自豪地管自己叫“上帝的人”。
英国作家毛姆以高更为原型,创作了小说《月亮和六便士》。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我认为有些人诞生在某一个地方可以说未得其所。机缘把他们随便抛掷到一个环境中,而他们却一直思念着一处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坐落在何处的家乡……说不定在他们内心深处仍然隐伏着多少世代前祖先的习性和癖好,叫这些彷徨者再回到他们祖先在远古就已离开的土地。”南岛语族的后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远涉重洋,一定是冥冥之中听见了来自原乡的召唤。
南岛语族指的是说南岛语系的庞大族群。南岛语系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主要在岛屿上使用的语系,其分布区域特别广,东到太平洋东部的复活节岛,西至印度洋西岸的马达加斯加,北抵夏威夷和台湾,南到新西兰,东西跨度超过地球周长的一半。南岛语系包括到种语言,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语系。现在全球说属于南岛语系语言的人口约有2.7亿人,主要的居住地包括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等,我国台湾的高山族和海南岛的黎族都属于这个族群。
南岛语族是一个海洋族群,他们的祖先在大航海时代开始以前,就早已捷足先登,发现并占领了南太平洋上几乎所有与世隔绝的岛屿,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上移民。他们披星戴月、乘风破浪,凭借高超的航海技术,向碧波万顷的太平洋扬帆而去。在他们眼中,汪洋大海并非凶险迷茫的深渊,而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蓝色大门。他们像海浪涌上每一个沙滩。每发现一座岛屿,他们便定居下来,安身立命,繁衍生息。数代之后,由于人口的增长,有的人留了下来,更多的人继续向前航行,寻找新的家园。太平洋上风云变幻,幸运的人发现了如大溪地般丰饶的天堂,也有一些不幸的人遭遇了不测,像浪花在礁石上撞得粉身碎骨。这个有如神话般的海上长征整整持续了几千年,直到年左右前,南岛语族的后代才完成了这一波澜壮阔的移民壮举。
在波利尼西亚民间有一项类似中国赛龙舟的民俗活动,据说就是为了纪念他们的祖先驾乘独木舟漂洋过海来岛定居。易立亚说,在波利尼西亚当地,关于祖先来自何方,一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他们的老祖宗是从南美洲漂过来的,另一种说法是来自亚洲。持第二种说法的人很多,说得也更具体。
年,挪威探险家托尔?海尔达尔仿照古印第安人木筏的样式制造了简易的木筏,与5个伙伴从南美洲的秘鲁出海,历时天,漂流海里,到达了波利尼西亚群岛的一个荒岛。他想通过此举证明,波利尼西亚的第一批居民是来自拉丁美洲的古代印加人,他们是在公元5世纪横渡太平洋到此定居的。他还将这段传奇的经历写成了纪实小说《孤筏重洋》。这本书受到了包括中国诗人海子在内的众多读者的推崇,也是寻根之路上陪伴易立亚的三本书之一,但是海尔达尔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呼应和支持。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线索:南太平洋诸岛上的原住民都说,他们的祖先曾告诉他们,他们祖宗的祖宗是从“北方的一个大岛”上来的。北半球岛屿星罗棋布,“大岛”究竟有多大,坐落在哪里?祖先没说清楚,也没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仅凭如此简单的线索去寻找,无异于大海捞针。
其实从20世纪初开始,国际学术界就开始孜孜不倦地为这个伟大的航海民族寻找故乡。考古学家根据拉皮塔文化(大洋洲最早的南岛语族文化)与菲律宾、印尼出土的陶器特征的相似性,认为这个“大岛”位于东南亚。后来,遗传学家在对太平洋地区41个族群中的个个体进行研究后惊讶地发现,台湾少数民族的遗传基因与波利尼西亚人惊人地相似,于是人们又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第一大岛屿——台湾。而且,历史语言学研究已经确定台湾少数民族的语言是南岛语族中最古老的语群。再后来,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出土了目前最早的有段石锛,有年左右的历史。石锛作为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石器工具,在中国东南沿海和东南亚海岛上都有分布,成为考古学家辨认南岛语族迁徙路线的重要依据。所以现在国际和国内的考古学界都将福建第一大岛屿——平潭视为南岛语族最早离开原乡的起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赞同“南岛语族起源于中国福建东南沿海,后经台湾岛向太平洋传播”的推断。
在昙石山博物馆,我见到了福建先民使用过的独木舟。在普通人眼中,那不过是块不起眼的木头,但考古学者却可以从它身上捕捉到不寻常的信息,甚至抢救出一个民族被湮没的历史。据说在年前,由于海平面上升,昙石山位于闽江的入海口。我的眼前浮现出了这样一幅画面:南岛语族的先人们驾着一叶叶轻舟,驶向烟波浩渺的大海。在一望无际的海上,他们显得那么渺小,犹如沧海一粟。我不禁想起台湾作家龙应台的一段话:“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所有的生死离别,都发生在某一个码头。上了船,就是一生。”而对南岛语族来说,这一别,就是五六千年。他们越走越远,再也没有回头。
三
在人类还很年轻的时候,古人对于海洋的探索,就像我们今天走向太空一样需要梦想和追寻梦想的勇气。南岛语族的先人将前程和未来交给了大海,他们乘坐独木舟,从闽江口、平潭岛出发,穿越台湾海峡,追逐着太阳和星辰,驶向了太平洋深处。他们倾听着大海的心跳和脉动,季风将他们送往了一个个孤悬海上的小岛。这是一首多么恢宏而浪漫的史诗!美国人类学家帕特里克?基尔希将这随风漂荡、随波逐流的漫长旅程形象地称为“风之路”。
福建位于世界上最大的大陆板块和大洋板块的交界处。夏季,受西南季风影响,舟船沿台湾海峡东侧航行就可以直接驶入东海,进入太平洋;冬季,受东北季风影响,舟船又可以轻易地驶向南海和印度洋沿岸。南岛语族的先人以无数生命为代价,发现并掌握了洋流和季风的规律。面对狂风暴雨和惊涛骇浪,他们从未望洋兴叹,而是劈波斩浪,在海上开疆拓土,成为大海的主人。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彼德?贝尔伍德勾画出了一幅南岛语族的扩散图。在大约年前,南岛语族通过简单的舟楫工具跨越海峡,来到台湾。在台湾,他们制造出了能够抵御巨浪、适合远航的船只,并在大约年前南下扩散到了菲律宾北部。在距今年左右,他们抵达了婆罗洲和印尼东部。然后往东西两个方向扩散,东到马里亚那群岛和南太平洋诸岛,西至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时间约在年前。在大部分南岛语族东进太平洋的时候,他们中的另一支,在大约年前却驶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跨过印度洋,来到了非洲东岸的马达加斯加。公元年左右,新西兰的毛利族成为南岛语族最晚的移民。
南岛语族的拓荒者和他们的后代在太平洋地区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但是随着时光的冲刷和民族的融合,许多文化和技术在迁徙和扩散的过程中失传或者被改变了,但一代又一代南岛语族人顽强地保留了自己的语言,即使在相隔千万里的海岛上,仍然可以用相似的语言进行交流,令人惊叹。
高更有一幅著名的油画,叫《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这一连串的自我追问是人类永恒的哲学命题。易立亚一行来到福州,是为南岛语族寻找答案的。他们用行动证明了他们的祖先来自中国,他们是福建先民的后裔。可是还有一个谜依然没有解开:他们的祖先当初为什么要离开古老的家园?是什么迫使他们义无反顾地走向海洋?
由于福建先民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没有留下任何记载,甚至连这片土地最早的主人如何称呼自己,也都无从考证。在先秦和两汉时期,历史是由中原的士大夫书写的,他们将那时的福建人称为“闽越人”,将其归类到“百越”之中,对福建发生的大事件往往点到为止,一笔带过。倒是古代地理志书《山海经》中的一句“闽在海中”赋予了我们无穷的想象。
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南岛语族远走他乡的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因为稻作经济传播导致的人口增长,有的将其与秦始皇统一中国时的“百越叛走”联系起来。我觉得我们有时把问题想得过于复杂了。对于南岛语族这个向往自由、四海为家的族群来说,他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无边无际的大海才是他们广阔的天地和生命的源泉。或许他们的远航只是为了探索未知的秘境、寻找更好的家园罢了。这是海洋族群所特有的性格使然,他们不安于现状,富于冒险性和开创性,渴望走出去,敢为天下先。正如“闽”字所透露出的意义:门里是条虫,出门是条龙。或许正是由于“闽在海中”,大海便成为一种信仰,是执着的信仰使南岛语族的先人们在万顷波涛上纵横驰骋,创造出了这史无前例的奇迹。
台湾作家钟理和在小说《原乡人》中写道:“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南岛语族的后人跨越千山万水,在福州找到了原乡,那么生在福州、长在福州的我们,原乡又在哪里呢?
《史记?东越列传》记载,公元前年越国亡国后,越王的后代逃亡到福建,建立了福建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闽越国(也有考古学家认为,闽越国是留守故土的南岛语族建立的)。闽越王叫无诸,所以闽越国又称“无诸国”。后来无诸的儿子余善造反,自封“东越武帝”。公元前年,汉武帝派兵剿灭了闽越国,将“无诸国”的男人们流放到江淮一带,将其妻女分配给汉兵为妻。于是那些被迫改嫁的“无诸国”的娘子就被称为“诸娘人”,而那些汉兵多为山西陶唐氏族人,故称“唐部人”。从此,南岛语族在福建便沦为了边缘化的族群。至今福州方言仍然用“唐部人”和“诸娘人”来称呼当地的男人和女人。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闽江沿岸曾漂浮着不少连家船,生活在船上的人被称作“疍民”,他们一生漂泊水上,以船为家,捕鱼为业。他们自称是闽越人的后代,为躲避汉兵的搜捕而流亡于江海。疍民有许多与岸上的福州人截然不同的习俗、礼仪和禁忌,历史上还曾有过自己独特的语言,至今他们所说的语言中还包含着少数疍民特有的词汇。他们或许是现在离我们最近的南岛语族。20世纪中叶以来,大批疍民上岸定居,传统的疍民生活方式逐渐萎缩。
从秦汉到三国,福建的民族结构开始发生变化。自晋经唐到宋,因战争、灾荒或避难而入闽的中原人络绎不绝。经过许多次民族融合,福建人口逐渐变成以汉族人为主体。经过长达多年的汉化,现在福建已经没有说南岛语系的人,早已被汉藏语系取而代之。所以现在大多数福建人的原乡在中国的北方,根在中原。在福建这片土地上,我们反而变成了异乡人。
打个简单的比方吧。南岛语族的回归,就好似几个陌生人风尘仆仆地找上门来,说这房子曾是他们的祖屋,而饱经沧桑的老宅子却早已易了主,将从前的主人拦在了门外。时光荏苒,物是人非。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停地背井离乡,又一直走在还乡的路上。因为乡愁是一棵树,你出生时它就扎了根,在身体里暗自生长。当你越走越远,总有一些老去的人劝你常回家看看,当你渐渐老了,总有一个声音在耳边提醒着你,要记得落叶归根。然而,有时候因为我们离开了太久,人世间发生了太多的变故,故乡便再也回不去了。但是无论身在何时何地,故乡早已成为我们生命中抹不去的胎记,正如易立亚在《航海日记》里所写的:“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我们看到的都是同一片天空。”
赞赏
转载请注明:http://www.xuefolanqc.com/gjqh/1604.html